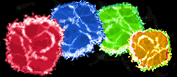我看蔡永生的《花窺》系列
 距離蔡永生今年初在台北東區 1839 藝廊所舉行的 《花窺》攝影個展結束已快要半年。一個男人將攝影機侵入具備性/別意涵的花卉,若在西方的女性主義論述語彙下將成為怎樣的闡釋與解讀?筆者佔且不將文脈往此方向推移。這批作品,巧合的是以"永生"為名的作者用攝影道出花卉生命的短暫,卻又以攝影的方式將花卉那短暫的生命成為"永生"。攝影總是如此 矛盾與徘徊於死亡象徵與瞬間永恆之間,遊走於表相真實與虛應故事之間。在經過筆者索討包含展出作品之外的其他數十張《花窺》影像並仔細觀看後,筆者以為蔡永生的《花窺》 開啟了一扇情慾之窗,似乎是一種透過東方含蓄般的感情修辭,透過攝影表現出如畫般的詩意與視覺語彙。
距離蔡永生今年初在台北東區 1839 藝廊所舉行的 《花窺》攝影個展結束已快要半年。一個男人將攝影機侵入具備性/別意涵的花卉,若在西方的女性主義論述語彙下將成為怎樣的闡釋與解讀?筆者佔且不將文脈往此方向推移。這批作品,巧合的是以"永生"為名的作者用攝影道出花卉生命的短暫,卻又以攝影的方式將花卉那短暫的生命成為"永生"。攝影總是如此 矛盾與徘徊於死亡象徵與瞬間永恆之間,遊走於表相真實與虛應故事之間。在經過筆者索討包含展出作品之外的其他數十張《花窺》影像並仔細觀看後,筆者以為蔡永生的《花窺》 開啟了一扇情慾之窗,似乎是一種透過東方含蓄般的感情修辭,透過攝影表現出如畫般的詩意與視覺語彙。宛如人體般的造形表現
就這整批影像的解讀、描述和銓釋而言,截至目前為止似乎只有陳敬寶先生爲《花窺》系列展出所寫的〈花/非花〉乙篇文章可供參考。在陳先生的文章中將這系列花卉攝影類比了其他國外攝影名家與畫家的花卉作品,並歸結了差異性(卻略過作品形式較類似的王小慧,而碰巧的是王小慧的其中一系列作品正以《花非花》為名)。就某部分而言,筆者同意蔡永生的花卉作品並非為求再現植物的生命美感,而是透過花卉拍攝創作表現出自身情感的轉化。
《花窺》系列最大的形式上的特色就在於大量運用了模糊和極淺的景深,甚至部份作品連畫面上是否有清晰的對焦點都不易察覺。而在西方攝影成為獨立的藝術形式並和其巒生兄弟繪畫作為區隔時,攝影藝術被賦予其的形式特色之一就是將畫意的,朦朧的表現手法從其中抹除,取而代之以清晰銳利的畫面形式。如歐陸的新客觀主義(Neue Sachlichkeit)以及美國的攝影/分離運動(Photo-Secession Movement)之後興起的純攝影(Straight Photography)以及受其風格所影響的後代攝影家與藝術家。作品本身誕生於不同的風格史與文化脈絡中,要在西方攝影史脈絡中找尋作品類比《花窺》系列,恐將如同把西方繪畫的透視法類比東方山水的謝赫六法,易生誤解並非必要。
作為《花窺》這批作品欣賞者的筆者,初次與之接觸的印象卻不自覺地聯想起人體攝影。如〈作品15〉中,整體花卉造型朦朧中就好似加了柔焦處理所拍攝出人體的肩頸部與髮絲線條。以攝影創作而言,人體的拍攝和花卉的拍攝其實有許多共同之處:透過鏡頭與構圖把三度空間的物體以二維平面的點線面構成,並且一樣可以玩轉於幾何造形與有機造形之間。如艾德華‧威斯頓(Edward Weston) 1936年作品 Nude,(227N) ,蜷曲的女體如同花瓣般造形就可見一般。
在西方古典藝術史中,人體的描繪主要旨在追求真善美與完美的幾何線條,因此與人體相關的藝術創作必非等同情色與愛慾(Eros)的追逐。然而東方的古典文化傳統中,裸身的女體卻往往等同於情慾的符號並鮮少出現在人物繪畫中。對比在西方攝影史中銳利清晰的人體線條造形所追求形式上的完美,《花窺》的柔軟與模糊所成形的有機造形則更適合將花卉陰柔化、情慾化的客體論述,而這也和作者本身的創作自述所契合。就一方面而言,蔡永生的花卉造形即便是有著上述般裸身的隱喻,但就另一方面而言,支撐其作品內在的感情部分卻是一種運用色彩的移情效果。換句話說,雖本非作者所圖,如果硬要把這批作品全部轉為黑白,部分作品中的造形將不足以承載花卉本身的視覺美感。或許這也是作者選擇下述色彩創作的原因。
 夢境、虛幻、暖色系
夢境、虛幻、暖色系《花窺》整系列的另一特色在於色彩的運用。若扣除無彩度的黑與白,包含未發表的其他數十張影像,整系列作品幾乎只有紫紅、紅、黃等顏色作明度變化的配搭。若以伊登十二色相環來看,這是一種相鄰色配色法:透過鄰近的色系創造突顯出和諧的視覺畫面。這些色彩都是暖色系,按照作者的說法則是為求一種擁抱般的浪漫氛圍與感情。
在部份作品的呈現中,本身已經是抽象的畫面加上暖色系的渲染,讓畫面的呈現頓失重力:成為一種如同真空般的懸浮飄移狀態。如〈作品28〉與〈作品29〉皺折般畫面,讓人聯想起人類要麼在太空或是在夢中,要麼就是在母體的子宮中才有機會如此抗重力的飄移。這夢境般的虛幻,也同時隱喻了生之慾。它們是否就綻放在激情邊緣?
 而在〈作品18〉與〈作品40〉中,微光照射半透明的花衣、透過幽微看見的,究竟是墓穴?或亦是柏拉圖的洞穴?筆者以為在這光影般的氛圍,所透射出的是一種少年維特般的詩情畫意:就如同德國電影《再見列寧(Good Bye Lenin)》中的男主角在醫院看到走廊上走動中的女護士,被強光穿越的裙襬中所顯露出的女體線條一般:即便是在不可見中依舊投射出內心的"渇見",隱藏的愛慾暈染滿溢而出。
而在〈作品18〉與〈作品40〉中,微光照射半透明的花衣、透過幽微看見的,究竟是墓穴?或亦是柏拉圖的洞穴?筆者以為在這光影般的氛圍,所透射出的是一種少年維特般的詩情畫意:就如同德國電影《再見列寧(Good Bye Lenin)》中的男主角在醫院看到走廊上走動中的女護士,被強光穿越的裙襬中所顯露出的女體線條一般:即便是在不可見中依舊投射出內心的"渇見",隱藏的愛慾暈染滿溢而出。 在這溫暖色彩的背後,似乎有上述這麼種類似超現實的視覺陳述。而這暖色系形成的夢境虛幻背後,是溫情?是愛情?是激情?或亦是色情?筆者倒不願意隨意結論,畢竟保留那麼點想像空間,也是這些作品最大的特色之一:它們可以提供你許多開放性的解讀,畢竟花朵羞澀的內在都已為你而開。誠如杜甫〈客至〉所言:『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就看你與之對飲,願醉幾回了。
在這溫暖色彩的背後,似乎有上述這麼種類似超現實的視覺陳述。而這暖色系形成的夢境虛幻背後,是溫情?是愛情?是激情?或亦是色情?筆者倒不願意隨意結論,畢竟保留那麼點想像空間,也是這些作品最大的特色之一:它們可以提供你許多開放性的解讀,畢竟花朵羞澀的內在都已為你而開。誠如杜甫〈客至〉所言:『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就看你與之對飲,願醉幾回了。歷史上的7月●映像咖啡顯影
綜合好文隨選
[TOP]